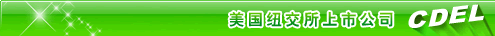甲流暴发,人人自危。各国政府在恐慌中买下了价值几十甚至上百亿美元的流感药物,虽然有研究表明这些药物并无特殊疗效。显然,在大家都为健康担忧的时刻,制药公司活得最为健康。对它们而言,这是一场利润的盛宴。
今年9月30日,英国卫生部免疫处负责人戴维·萨利博瑞教授给各地卫生部门和全民公费医疗体系基础护理机构负责人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新的流感疫苗要三周后才能大量供应,而且短期内货量都不够。当时,在一个夏天的消停之后,英国的流感暴发率再次上升。萨利博瑞的信发出两周之内,新增病例较之前两周增加了一倍,25岁以下病患增长速度创下纪录。
萨利博瑞提到的疫苗并非常规的流感疫苗,而是由葛兰素史克专门针对甲流制造的,名为Pandemrix.萨利博瑞希望能为950万临床高风险人群———老人、孕妇、免疫能力欠缺者、心脏病患者,以及医疗卫生工作者———接种这种疫苗。理想状态下,应该是在三周时间内接种两次,但据说打一次足以提供充分的保护。信里谈到了这种疫苗的成分,包括用来保证稳定性的汞元素。他也提到,新疫苗仅用四个月就研发出来,比常规流感疫苗推出时间少两个月。虽然大部分人接种后没有不良反应,但也有少数人会产生副作用,这些“受害者”会有“疫苗伤害补偿计划”予以保障。
最后,萨利博瑞表示,对抗甲流的战争远未结束。“我要谢谢你们迄今为止所做的一切,”他写道:“我肯定你们还会继续战斗下去。”
这封具有浓重战时公告味道的信标志着英国“甲流之战”的转折点。它有种让人安心的感觉:一切都在控制之中,科技会带领我们安然度过危机。也许事情会变得更糟,但我们已经做好准备。
但事情还有另一面。人们之所以松了一口气,部分是因为迄今为止,甲流在英国的发展不像原来预期的那样有灾难性:四月末英国出现首例病例后,流行病学家预计感染者将迅速增长,很快就会达到每天新增10万患者的地步。英国卫生部长想象的最糟状况是:30%的英国人被感染,65000人死亡。而如今根据统计,到10月中旬为止,英格兰有83例死亡,苏格兰15例,威尔士4例,北爱尔兰4例。整个英国估计有37万人感染。
另外一个原因是,与过去50年里夺走数百万人性命的三次重大流行病相比,我们总算暂时挺了过来,虽然我们现在拥有的药物只不过稍微好了一丁点。过去六个月来,达菲和瑞乐莎一炮走红,像立妥威和百忧解风行于1980年代,万艾可独领风骚于1990年代一样,估计它们也会占据十余年的统治地位,但却是出于错误的理由:针对病人的调查表明,这些药充其量只是略有效果。在大部分患甲流至少一周的病例中,服药后病程只是缩减了半天到四分之三天。如果没有在最初48小时内服药,效果还要打折扣,甚至毫无效果,结果就是副作用超过了好处。
制药商从未隐瞒药物的疗效,或者它“没疗效”。但从2006年以来,各国政府还是购买了大约2.7亿个疗程的达菲,其中一半是在过去6个月内售出的。葛兰素史克开足马力,准备到年底增产1.9亿个疗程的瑞乐莎,这是其平常年产量的三倍。7月23日到10月7日,英国新设的国家流感服务中心在英格兰发放了64.4万个疗程的此类抗病毒药物。该中心开设前三个月内,药物主要通过基本护理机构开出,估计也有几十万个疗程。自2005年启动流感应对方案以来,英国政府花了5亿多英镑购买抗病毒药物和疫苗。卫生部没有公布甲流药物在其中占了多大份额,但购买达菲和瑞乐莎的费用至少占这些支出的一半。这急切的囤积行为不可避免地推高了罗氏制药和葛兰素史克等制药公司的收入与股票价格。
这带来了一些问题:卫生官员是不是太急于在危机中稳定民众情绪,以至于把明知是二流的药物发放出来?我们是不是在仅比安慰剂强一点的东西上花了太多钱?10年前,英国国家卫生医疗质量标准署审查这些药物时,因其效果不够显著而拒不批准,现在我们又该如何解释政府和医院的狂热行为?9月份英国卫生部还明确发布指导方针,要求医生在治疗普通流感时既不要开达菲也不要开瑞乐莎,这又如何解释?如果这些药物连普通流感都无法应付,那它们在甲流面前又有何德何能?
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绝望。尽管医学取得了令人叹为观止的进步,我们仍然连那些司空见惯的普通病毒都对付不了。每年这些病毒都会产生基因变异,无法控制。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惨痛的失败。而流行病则把这种失败放大无数倍,以至于政府被迫采取行动,虽然他们知道行动也未必有什么效果。只是,这样做是否明智?它会否令我们的健康更加恶化?
自从1918至1919年西班牙流感暴发夺去多达5000万人的生命,治愈流行性感冒就成了医学界可望而不可即的“圣杯”。很多制药公司都知道,若能征服流感,就等于拥有一棵巨大的摇钱树,但他们逐渐意识到,自己面对的不是一个敌人,而是变幻无穷的军团。平均每个冬季,英国都会有3000到4000人死于流感并发症,其中大部分是老人,全球因此死亡者约为10万人。而当有新型流感出现时,后果更是难以预计。亚洲型流感(1957年)、香港流感(1968年)、俄罗斯流感(1977年)的大暴发都影响到了整个城市的运转,1997年,香港毫不手软地杀掉了几十万只鸡鸭,人们总算勉强地躲过了禽流感的毁灭性打击。但是,“老大”可能还潜伏在角落里:世界卫生组织一直警告说,因为流感病毒不停变异,暴发人类完全无法应付的毁灭性流行病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很有可能的。
我们现在知道,大部分情况下甲流症状与普通流感无异:四肢酸痛、头痛、咳嗽、发烧、冷汗、没有胃口、恶心。但即使是对一个身体不错的成年人来说,这些症状搅和在一起,也是够难受的。所以只要还能起床,人们就会想尽一切办法结束病痛,因此连最平庸的药物也被渴望痊愈的人们当成宝贝。问题是,我们现在吃下肚去用来治疗甲流的药物不是在这种焦虑情绪中刚刚生产的,它们是1980年代初在澳大利亚一个实验室偶然出现的。回顾它们进化和出名的过程,我们就会明白:人类对流感所知甚少,战斗将一直持续下去。
1983年,在墨尔本,受雇于澳大利亚联邦科学与工业研究组织的病毒学家彼得·科尔曼正试图理解流感病毒是如何年复一年发生变化的。这是个孤独的工作:病毒变异如此频繁,人们普遍认为没有药物赶得上它的脚步。大部分科学家和制药公司都已放弃了寻找“万灵药”的努力。但科尔曼在研究过程中有了一个超越前人的发现,那就是病毒有一个方面始终不会变化。
流感病毒表面布满两种重要蛋白质:血凝素把病毒固定在人体健康细胞中,神经氨酸酶则负责分解病毒,将之释放出来,感染其他细胞。多年来,科学家们都致力于制造“神经氨酸酶抑制剂”,以控制病毒扩散,但是因为对这种蛋白的结构和行为方式缺乏了解,屡屡受挫。
“当时人们已经厌倦了,”科尔曼回忆说,因此当他发现神经氨酸酶可以作为固定的靶点时,“那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
一开始外界没有什么反应。一年多之后,墨尔本一家新成立的Biota控股公司总算有了兴趣。CSIRO同意把科尔曼的成果授权给Biota开发,条件是只要有任何药物上市销售,都要收取特许使用费。又经过三年的研究,Biota证实了科尔曼的结论,也就是使用神经氨酸酶“堵塞药物”可以阻断流感的传播。该公司设计了数千种可能有用的配方,但因为它的实力太过弱小,无法进行大规模的实验。所以1990年2月,它与英国公司葛兰素史克合作,将数据移交给后者。
接手的是年轻的酶学家理查德·贝塞尔博士。1989年加入葛兰素史克时,他没想到自己要主攻流感。那时他所在的病毒部几乎把所有精力都放在HIV上。“自1960年代以来,流感方面就没有什么新发现,”他回忆说。药物三环癸胺对A型流感部分有效,但是它颇有些副作用,而且病毒早就对它产生了耐药性。
“我们等于是从头开始,”贝塞尔回忆说。他们研究出一种化学方法,对Biota公司那几百种配方进行检验,发现还是第一批次中某个方子最为有效。它编号GG167,取了个商品名叫zanamivir,是最早完全在电脑上研发出来的药物之一。
问题是神经氨酸酶不仅存在于流感病毒中,也存在于人类细胞中,正常发挥作用。药物必须强大到足以杀死流感,但又不要影响到人体自身。贝塞尔亲自参加了安全实验,欣慰地发现要很大剂量才会影响到人体内的神经氨酸酶:“zanamivir对流感病毒中的神经氨酸酶的作用力是对正常神经氨酸酶的100万倍。”这是一个突破。“只有这个结果出来之后,我们才敢相信这个配方是安全的。”
动物实验始于1993年;第一批志愿者1994年1月接受感染,这是20多年来首次有流感药物进行临床实验。当结果反馈回来,“他们都很兴奋,”贝塞尔回忆说:“不管是用于预防还是治疗,药物都非常有效。他们不再咳嗽、没完没了地擤鼻涕。服用了zanamivir的人没有发烧。控制组的人却很惨。”
接下来在美国、欧洲、南非和新西兰自然感染流感的病人身上做了实验。结果同样令人印象深刻:与什么药也没吃的病人相比,出现症状48小时内用药的病人症状要早消失一天到两天半。
“肯定不是吃两片药马上就没事了,”贝塞尔说:“一旦有了症状,病毒就占了上风,但哪怕有30%到40%的改善,也很好了。”在提交给欧洲药物监管机构申请批准之前,葛兰素已经在大约3000名病人身上做了实验。实验结果公布后,该公司股价飙升。到1999年末,投资分析家估计,光是在美国,其流感药物年产值就在50亿美元左右。
但问题依然存在。在实验了几种zanamivir使用办法后——注射、口服或吸入——葛兰素的研究者发现它在血流里的分解度很差,生物药效率较低。唯一有效的办法是使用该公司专利产品Diskhaler.“这是一种简单的呼吸启动式吸入器,”贝塞尔说:“用起来跟吸烟一样容易。”
但对zanamivir的推广来说,Diskhaler始终是个障碍。尽管与口服相比,吸入方式更有利于药物进入肺部,锁定病毒繁衍区域,但这个过程毕竟繁琐,不太方便。何况,得一次流感,一般要连用五天zanamivir,每天两次。
不过,zanamivir市场化步伐还是在加快。葛兰素开始向NHS介绍这种新药,并给它取了个更容易记名字瑞乐莎(Relenza)。与此同时,葛兰素员工最大的恐惧将要成真:一种作用机理跟瑞乐莎很像、但可以口服的药就要面世,它就是达菲。
自1994年葛兰素早期实验结果,位于圣弗朗西斯科附近的小型生物科技公司Gilead Sciences就对神经氨酸酶抑制剂产生了兴趣。“我们之前就有流感药物研发项目,”时任Gilead高级主管的庄恩·吉姆告诉我:“但是我们决定转向,一个原因就是葛兰素的药物不便口服。我在药物研发业工作了25年,看过很多抗菌药物的发展,有注射的,有口服的,也有吸入式的,但到最后,大赢家都是口服药。”
Gilead公司的产品——编号GS4104,后取名oseltamivir——很快吸引了瑞士制药巨头罗氏公司的注意。由于是口服,oseltamivir的设计与瑞乐莎完全不同,但基础结构同样借鉴十年前科尔曼的研究。而且,在电脑设计模块的帮助下,Gilead改进得很快。1995年初,它已经拿出了适合进行临床实验的药物。一开始是动物实验,在白鼬身上的生物药效率令人失望,但在狗身上几乎是100%有效。人体实验结果与zanamivir一样好,虽然一些病人报告说有恶心、呕吐等副作用。
一般药物从开始计划到完成人体实验至少需要10年,oseltamivir只花了三年。“我们最大动力就是必须追上葛兰素,”吉姆说:“罗氏知道与葛兰素同时将药投放市场———或者只慢一点——是多么重要。”
十年前我第一次跟这些新药缔造者对话时,他们毫不掩饰自己的成就感。“我们很激动!”Gilead公关经理苏珊·哈伯德说。“整个团队都飘飘欲仙,”贝塞尔说:“我们都认为它是神药——最有效,最安全。”
然而时移世易。达菲和瑞乐莎从2000年起大量供应,但直到最近六个月才被广泛使用。七月末一周时间内,10万多个疗程的抗病毒药物在英格兰发放,这样大规模的服用不可避免会带来问题。10%的使用者报告说有副作用,特别是呕吐、头痛和腹泻,虽然你很难区分这是药物的不良反应还是病情本身的结果。也有人担心孕妇和12岁以下人群使用这些药物是否安全,最近还有实验室数据表明甲流病毒开始对达菲产生耐药性。对达菲和瑞乐莎进行的测试越多,结果就越不乐观,人们对它们怀抱的期望在消退。
有趣的是,警告从一开始就有。1999年Nice刚成立时,第一个考察对象就是瑞乐莎。它用了几个月时间分析瑞乐莎的实验数据,最后决定不推荐这种药物。一年后,它又拿出了另一份令人气馁的报告,称药物可能对成人中的高风险人群——65岁以上,或患有慢性呼吸或心脏疾病,或1型糖尿病患者———有效,前提是出现症状48小时内使用,但结论是:NHS不应使用zanamivir治疗普通流感患者。对达菲,Nice的态度也是一样。
2006年一个国际调查,声称瑞乐莎和达菲对于已确定的特定病毒有疗效,但不推荐把它们作为普遍治疗药物使用。发表在2009年9月的另外一项研究则发现,健康成年人患病后服用瑞乐莎,流感症状只缩减了0.57天,服用达菲则缩减了0.55天,而十年前葛兰素估计病情会缓解“30%到40%”,两相对比,差距实在不小。对于那些有并发症风险的患者来说,疗效会稍微好一些:服用达菲者流感症状缩减了0.74天,服用瑞乐莎者缩减了0.98天。最后它再次得出人们熟悉的结论:“在控制健康成年人季节性流感方面,对呈现出症状者使用抗病毒药物治疗并非最恰当的做法。”2009年2月Nice发布的最新指导方针引用了这些发现,建议只对风险人群使用神经氨酸酶抑制剂,即便在甲流暴发后,这一指导方针也未改变。
如何解释在科学家的极高期望之下,这两种药物表现出来的低效?一名曾多年从事流感治疗的著名病毒学家说:“神经氨酸酶抑制剂展示了仅能阻碍病毒复制的药物的局限性。有证据表明,症状开始出现时,病毒在人体内的复制活动已达到最高峰。事实上等药物进入人体开始发挥作用时,病毒水平已经开始下降。”
那又如何解释英国过去6个月内就开出大约100万个疗程的达菲和瑞乐莎的行为?支持政府的人给出了很多答案。首先是防患于未然,如果卫生部不作为,可能导致潮水般的批评;其次就是人类有希望得到保护、远离病痛的天性。在这样一个受到大规模监管的年代,他们至少也希望得到大规模的宠爱。“如果告诉英国人民,我们有足够的药物储备,但他们却享用不了,人们肯定不能接受,”英国大流行性感冒伦理事务委员会成员罗伯特·丁沃尔教授说。
政府并不讳言其过量开药的做法。“由于不知道新的病毒何时暴发,”7月2日NHS首席执行官戴维·尼克尔森在致员工的一封信中写道:“采取所有可能手段减缓其扩散是明智的。”这些手段包括隔离疑似患者,不仅向确诊患者提供达菲和瑞乐莎,也向与患者有接触、但还没有症状的人发放,不仅包括患者的亲戚朋友,也包括其同学和同事。
6月11日世界卫生组织将流感预警信号提到最高的6级水平,此后英国放弃了“围堵政策”。7月16日,内阁紧急事务委员会发布最新预期,估计在最糟情况下,到9月份将有30%人口被感染,占全部劳动力的12%,最终被感染人口比例可能高达60%,患者死亡率则可能高达0.35%.展望这种末日画面,政府加快了囤积抗病毒药物、免疫注射的步伐。
“我们知道不可能彻底防止或牵制病毒的传播,”尼克尔森写道:“因此大臣们都同意,该从围堵走向治疗了。”在这个阶段,政府向未出现症状者发放的药物量会减少,但建立了NPFS.病人可以通过电话或网络联系NPFS,回答一系列问题,如果被确认有甲流症状,就可以得到一个编码,凭它到当地药剂师那里领取达菲或者瑞乐莎。这种全新的医疗模式很容易出错或受到欺诈,有报道说那些热线是由没受过多少培训的十几岁孩子接听的,无奈英国已经全民患上甲流“癔症”:旅游业一蹶不振,打算出国的人非得先在行李箱内塞满达菲才肯动身,网络黑市繁荣,不少夫妇准备等甲流退潮后再要孩子,BBC因为替海外员工囤积达菲受到指责,报道说,“医生希望医院门口有警卫把守,因为有些患者家属要求开药被拒时会变得很暴力。”
而从商业角度看则是另外一番光景,葛兰素的盈利扶摇直上。英国第一例甲流确诊后那一周,它的股价上升了8%,Biota的股价则上涨了16%.六月末,瑞乐莎的销售增加了9900万美元,与2008年第二季度的500万美元有天壤之别;10月中旬,罗氏报告说,2009年头9个月,达菲约销售了20亿瑞士法郎,与去年同期相比上升了362%.
10月初我参观葛兰素史克时,很为其气势所震惊:位于伦敦西部的公司大楼是个由玻璃和金属构成的庞然大物,大厅忙忙碌碌的热闹景象完全符合你对全球第二大制药公司的想象。我到那儿去是为了见约翰·迪隆先生,葛兰素流行病中心的医学主管。他敏锐地指出,瑞乐莎非常有用,没有明确证据表明甲流病毒已对它发展出耐药性。然后我们谈到了备受争议的疗效问题,他说:“没有根治流感一说”,强调只要能缓解症状就是受欢迎的,并向我展示了一种更简单的瑞乐莎服用办法,用的是胶囊。
随着谈话进一步深入,我发现对这里的人而言,瑞乐莎已经不是治疗甲流最重要的选择。公司将把疫苗Pandemrix大量运往世界各地,各项准备已进入最后阶段。到10月份第一周为止,公司已经收到全球4.4亿剂量的订单,较六周前增长了1.49亿剂量。老的药物仍会有人用,当然效果也有限;而现在又有了一种新的办法,在这个不可预知的世界里捍卫我们的健康,直到被后来者代替。